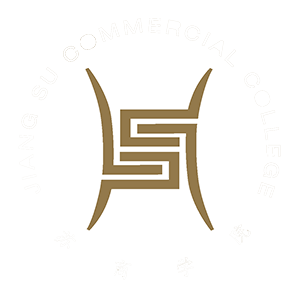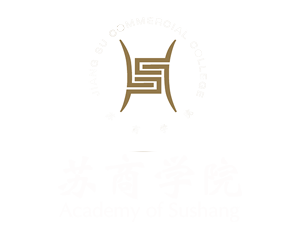自2014年“中國制造2025”戰略發布以來,我國制造業以“創新驅動、質量為先、綠色發展、結構優化、人才為本”為核心,完成了從規模擴張到質量躍升的轉型。十年間,我國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實現了五大標志性突破,這些成就不僅重塑了國內產業格局,更深刻影響了全球產業鏈分工。
第一大成就:全球制造業比重躍升,質變與量變并舉
我國制造業規模自2010年超越美國成為“全球第一”后,已連續多年穩居“世界第一”,并持續擴大領先優勢。2024年占全球制造業比重達34%,是美國的2倍、歐盟的3倍。這一成就不僅體現在規模上,更在于質的突破。2010年,我國制造業以中低端產品為主,依賴低成本競爭;而如今,在十大重點領域(如高端裝備、新能源汽車、芯片、船舶制造等),我國已從“跟跑者”逐步轉向“并跑者”甚至“領跑者”。
一是規模優勢鞏固。從1980年僅占全球制造業的2%,到2024年的34%,我國用4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百年的工業化道路。
二是技術突破密集涌現。有3個產業案例:第一,芯片產業,美國的技術封鎖倒逼我國自主創新,14納米制程芯片實現量產,7納米技術進入試產階段,2024年國產芯片出口規模達1500億美元左右,首次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第三大芯片供應國。第二,船舶制造,我國占據全球55%的造船訂單,液化天然氣(LNG)運輸船國產化率從10%提升至90%,突破“瓦錫蘭鋼板”等核心技術瓶頸。第三,超高壓輸電,我國掌握±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技術,輸電損耗僅為歐美傳統技術的1/10,成功將新疆的風電輸送到長三角,并推動“全球能源互聯網”倡議落地。
三是國際標準話語權提升。在5G通信、高鐵、新能源等領域,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占比從2015年的12%提升至2024年的35%。
而這一階段的標志就是我國制造業從“被動跟隨”轉向“主動引領”,在部分領域甚至成為全球技術規則的制定者。
第二大成就:產業鏈集群優勢凸顯,覆蓋全球最全工業門類
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工業分類中全部41個大類、207個中類、666個小類工業門類的國家。這種“全覆蓋”優勢使我國能夠快速形成產業鏈集群,實現“積木式”組合生產。例如,快速響應能力,疫情期間,我國憑借完整的產業鏈,在3個月內實現口罩日產能從2000萬只提升至10億只,呼吸機產量占全球80%。成本控制優勢,以智能手機為例,深圳華強北可在48小時內集齊一部手機所需的2000多個零部件,綜合成本比印度低40%。技術協同效應,像我國的盾構機,從完全依賴德國進口到國產化率超90%,并出口至歐洲市場,價格僅為進口設備的1/3。又比如新能源汽車產業,比亞迪、蔚來等品牌在2024年的出口量突破600萬輛,動力電池全球市占率超60%,寧德時代研發的鈉離子電池成本較鋰電池降低30%。值得一提的是,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從破土動工到首批Model 3交付僅用了10個月,帶動長三角形成涵蓋電池、電機、自動駕駛系統的千億級產業集群。另外,我國的光伏產業占據了全球70%的產能,并在超高壓輸電技術支持下,構建全球清潔能源供應網絡。
這種集群效應不僅降低了綜合成本(如蘋果手機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比美國低30%-40%),還吸引了外資持續涌入。2023年,我國實際使用外資超1600億美元,特斯拉、三星等企業通過“產地銷”模式深度融入我國市場。
第三大成就:出口結構優化,高附加值產品主導全球貿易
我國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:2010年,70%的出口為勞動密集型產品(如服裝、玩具);而到2024年,90%的出口轉向裝備類和電子類高附加值產品。首先,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大幅下降,像紡織服裝、玩具等傳統類商品的出口占比從2010年的70%降至2024年的10%。其次,高技術產品成為主力,我國的汽車出口從2017年不足100萬輛躍升至2024年的600萬輛,超越德日成為全球第一;像高鐵、盾構機、核磁共振設備等高端裝備實現技術自主并打入國際市場;在數字服務方面,我國迅速崛起,華為5G基站全球市占率超35%,抖音海外版TikTok用戶突破20億,阿里云成為亞太最大云計算服務商。
這一轉變使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顯著提升,徹底擺脫了“用10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”的被動局面。世界銀行數據顯示,我國制造業出口附加值率從2010年的65%升至2024年的82%,逼近德國水平。
第四大成就:生產方式升級,從“加工貿易”到“自主創新”
我國制造業生產方式實現了歷史性轉型:加工貿易占比從2010年的60%降至2024年的20%,一般貿易占比升至60%以上。這一變化帶來三大效益:第一,貿易結構優化,加工貿易占比從2010年的60%降至2024年的20%,一般貿易占比升至65%。第二,增加值率提升,一般貿易的GDP貢獻率是加工貿易的3倍,以智能手機為例,蘋果代工環節僅占整機價值的5%,而華為自主研發的Mate系列手機國內附加值率超60%。第三,抗風險能力增強,2023年中美貿易戰中,我國憑借完整的產業鏈抵御外部沖擊,特斯拉、三星等企業反而將在華投資增加20%。
在這一階段,我覺得標志性事件應該是“富士康現象”的終結。2024年,我國代工企業營收占比降至15%,而專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業數量突破2萬家,貢獻了35%的出口增量。我國制造業從“兩頭在外”的依附模式,轉向以內循環為主體、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。
第五大成就:外資深度融入,開放水平邁向更高層次
中國制造并不是“閉門造車”,十年間引進的外資比上一個十年翻了一番,對外開放勢頭非常好。2024年,外資企業貢獻了全國15%的稅收、30%的高端裝備出口和50%的服務貿易附加值。我國并未因技術自主而封閉,反而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吸引外資,形成了“以市場換技術”的良性循環。外資結構優化方面,企業研發中心的占比從2010年的10%升至2024年的40%,特斯拉上海創新中心每年申請專利超500項。本土化協同創新方面,半導體領域的ASML向中芯國際出售28納米光刻機,條件是必須與長江存儲聯合開發下一代存儲芯片。生物醫藥領域的輝瑞在上海設立全球第二大研發中心,與藥明康德合作開發針對亞洲人群的特效藥。這一階段的外資政策凸顯“精準開放”,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(負面清單)從2017年的63項縮減至2024年的27項,但關鍵領域(如稀土開采、基因編輯)仍保持嚴格管控。
站在“十四五”收官與“十五五”規劃啟動的歷史節點,我國制造業需瞄準新質生產力布局未來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應聚焦“三大賽道”:“1+10”產業鏈集群模式、傳統產業綠色智能化改造、生產性服務業升級,以此推動我國現代化邁向更高水平。
第一大賽道:“1+10”產業鏈集群,搶占五大新興領域
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在于“集群化創新”,即圍繞五大新興板塊(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交通、新生物醫藥、新人工智能數字化與高端裝備),構建“1個核心產業+10大生產性服務業”的生態體系。
新材料板塊,要突破瓶頸,支撐產業升級。像半導體材料行業,要加速碳化硅、氮化鎵等第三代半導體量產,打破日本在光刻膠、大硅片領域的壟斷。生物材料產業,要推進可降解塑料、人工骨骼產業化,預計2030年市場規模達萬億級。超導材料產業,要聚焦核聚變裝置所需的低溫超導帶材,我國在西南聚變工程試驗堆(SWIP)已實現關鍵突破。
新能源板塊,要構建零碳能源體系。我國在內蒙古庫布齊沙漠建設全球最大光伏基地(裝機容量1億千瓦),通過特高壓直送京津冀,掀起了光伏革命。在氫能方面做了提前布局,在成渝地區打造“氫走廊”,規劃2030年燃料電池車保有量突破100萬輛。此外,我國還在核聚變領域進行了攻關,我國的“人造太陽”EAST裝置已經實現了1億攝氏度運行100秒的突破,領跑全球核聚變研究。
新交通板塊,要重塑未來出行方式。自動駕駛現在勢頭正盛,百度Apollo、小鵬汽車在L4級自動駕駛領域實現城區道路全場景覆蓋,2025年有望取消方向盤法規限制。低空經濟產業潛力巨大,億航智能已經獲得了全球首張載人eVTOL適航證,深圳也在規劃建設20個垂直起降機場。超高速磁懸浮領域也有眾多項目,例如滬杭磁懸浮線啟動建設,時速600公里,30分鐘連接上海與杭州。
新生物醫藥板塊,要攻克生命科學前沿。生物醫藥目前主要分為基因編輯、AI制藥、精準醫療等方向。例如,北京啟函生物正利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培育出抗藍耳病克隆豬,推動畜牧業變革。晶泰科技則是通過量子計算+AI模型,將新藥研發周期從5年縮短至18個月。華大基因建成了全球最大人群基因組數據庫,癌癥早篩準確率已高達99%。
新人工智能數字化與高端裝備板塊,要去定義智能制造新標準。目前,埃斯頓已經突破諧波減速器技術,人形機器人制造成本降至10萬元以內。華為已經聯合中國移動完成了太赫茲頻段測試,理論速率達1Tbps,可以稱之為6G通信,這為元宇宙奠定基礎。本源量子早前發布例如72比特超導量子芯片,已經在金融風控、藥物模擬領域實現商用。
每個產業集群其實都需要配套十大生產性服務業——研發設計、供應鏈金融、檢驗認證、數字營銷等,形成“微笑曲線”全生態。例如在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,就聚集了CXO企業300余家,實現從靶點發現到臨床申報的一站式服務。
第二大賽道:傳統產業改造,綠色與數字雙輪驅動
目前,我國80%的工業存量需要通過綠色化、數字化來實現“老樹發新芽”。
綠色化改造要從被動治理到主動增值。比如鋼鐵行業,要去推廣電爐短流程煉鋼,噸鋼碳排放可以從2.1噸降至0.6噸,首鋼曹妃甸基地就建成全球首個“零碳鋼廠”。寶鋼的湛江基地通過“黑燈工廠”改造,煉鋼全程無人化,生產效率提升50%,噸鋼能耗下降30%。又比如化工行業,萬華化學已經開發出了CO?制甲醇的技術,每年可消納工業廢氣1000萬噸。另外,循環經濟也值得關注,像格林美目前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動力電池回收網絡,鎳鈷錳回收率超95%,較礦山開采成本低40%。
數字化改造則要從單點突破到系統重構。可以從工業互聯網、數字孿生、AI質檢等方面著手,工業互聯網領域做得比較好的是海爾的卡奧斯平臺,目前連接企業超過15萬家,幫助中小企業平均降本20%左右。數字孿生領域,我國商飛成功利用數字孿生技術,將C919試飛次數從3000次壓縮到了800次。AI質檢領域的典型則是京東方,他們應用AI視覺檢測技術來檢測面板缺陷,準確率從原來的90%提升到了現在的99.9%,每年可以節約成本超10億元。
第三大賽道:生產性服務業崛起,打造經濟增長新引擎
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升級的“倍增器”,需從三方面突破:第一,服務貿易要從“賣商品”突破到“賣標準”。技術出口、標準輸出、知識付費等方面大有可為。華為通過技術出口,向德國博世授權5G工廠解決方案,單筆合同金額達20億歐元。而我國主導制定的IEC特高壓標準已經被76個國家所采用,每年可以收取的專利費超過50億美元。又比如三一重工的“根云平臺”就很好地利用了知識付費,為海外客戶提供設備預測性維護服務,毛利率達到了70%。
第二,獨角獸培育則需要聚焦“微笑曲線”兩端。藥明康德打造了全球最大藥物研發外包平臺,通過研發服務收取服務費,年收入增長均達到40%。SHEIN在品牌運營方面,通過大數據精準預測歐美時尚趨勢,目前估值超1000億美元。螞蟻鏈則是利用供應鏈金融,為中小企業提供基于區塊鏈的跨境結算服務,將賬期縮短到3天。
第三,產業鏈服務化要從制造商升級到方案商。施耐德模式和海爾模式值得大家學習。施耐德是從電氣設備商轉型為能效服務商,服務收入占比超過了60%。海爾的卡奧斯平臺則是通過向陶瓷、紡織等行業輸出數字化方案,成功孵化出了15個垂直行業生態。
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發現,美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50%,而我國僅占27%,如果提升到40%,那么就可以釋放大約30萬億的增長空間。
最近,世界格局動蕩,在面對中美博弈、技術封鎖、全球產業鏈重構等外部挑戰時,我國制造業需要堅守五大戰略支點:第一,我國有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,有14億人口和4億中產形成的消費升級需求;第二,全產業鏈優勢,我國的41個工業大類、666個小類的協同能力不可小覷;第三,新型舉國體制,我國的國家實驗室、大科學裝置對“卡脖子”技術正在集中攻關;第四,數字基礎設施優勢,目前我國的5G基站超300萬座,算力規模是全球第二,這些都是底層支撐;第五,制度型開放,我國的自貿試驗區、RCEP協定構建的雙循環樞紐也是重要支點。
制造業是我國立國之本、強國之基。未來十年,是我國從“制造大國”邁向“制造強國”的關鍵期,只有以“1+10”產業鏈集群創新、綠色智能改造、生產性服務業升級為抓手,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制高點。
歷史經驗證明,封閉將導致落后,開放才能帶來繁榮。我國制造業的崛起不僅僅是技術的勝利,更是制度與道路自信的體現。在新時代的征程中,我國企業需以“釘釘子精神”攻克核心技術,以“鏈式思維”整合全球資源,最終實現從“中國制造”到“中國創造”的華麗轉身。